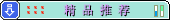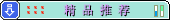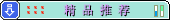 |
冷落清秋
冷落清秋
(一)
送她走的那一天,我明白我的婚姻也快到头了。
认识清是在我出国留学的前夕,那时候的我踌躇满志。
“粗柳簸萁细柳斗,世上哪有男儿丑?”是我的信条,我相信男人不在貌而在才。正如丑女才炫耀学问,只有蠢男才吹嘘容貌。
作为男人,我不属于长相出众的那一类,也许因为我个子不高吧。我也看不上那些女里女气的奶油小生。男人的魅力在于学问,而女人,恰恰相反,女子无貌才是才,无才便是德。“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在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和平时代,读书才是男人的立足之本。不是我自吹,我六岁入蒙学《唐诗三百首》《声律启蒙》《朱子家言》《古文观止》,如今即使称不上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差不多。只是时候未到,好马不见伯乐,韩信未遇沛公。
在大学里,我有不少哥们,晚上熄了灯就是吹牛扯皮谈女人。小时候的家学渊源倒从没有辜负过我的自信心甚至虚荣心,只闲扯一下《东周列国志》,管仲范蠡百里奚,苏秦张仪吕不韦,纵横捭合,再联系一下当前的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云云,洋洋洒洒,侃侃而谈,把同宿舍的哥几个就镇得哑口无言。至于《史记》《汉书》《隋史遗文》《唐通史》那些个存货连拿出来过过秤的机会都没有。别说男人爱吹,吹牛也是门学问。秀才不怕衣衫破,就怕肚里没有货,没有家底的胡吹不可能象我一样后面赢得一班助拳捧脚的。
总恨女人尤其那些美女眼皮子浅,看不到我这块真金。大学时我的艳遇不多,小女生和男人一样,也是以貌取人。跟哥们自吹也曾勾到过几个校花级美女,可惜美女的性子往往太差,消受不起。我的话也不完全是胡吹,我确实辅导过一个美女的数学,可惜那妞太笨,自己学不通,临了还把我开了。男人可以不要(漂亮的)脸,但绝对不能不要面子。哥们几个倒没有不赞成我聪明的。
九十年代的大学,金钱统领一切。我知道,这年头,光凭在校报上发几首情诗做个校园诗人,在女生楼下弹弹吉他做个流浪艺人是吸引不了多少异性的眼球了。要想赢得美人归,对我来说,只有一条路,出国。
别的可以吹,但托福GRE是吹不出来的,还真得下一番功夫。我在读硕士的最后一年,除了准备毕业论文,便是专心复习英文,考试,接下来就是申请学校的折磨。
我知道,一旦拿到学校录取通知,离出国的时间就不多了,这一段时间我必须抓紧找个女朋友。我真恨不能把GRE成绩贴脑门子上在女孩子们中招摇,那样我就不用这么费尽心机了。
曾跟哥们开玩笑,说起女朋友的条件,第一自然是漂亮,第二也是漂亮,第三还是漂亮。女人漂亮是男人的体面,还是那句话,男人可以自己不要(漂亮的)脸,但不能不要面子,即使需要打肿脸也在所不惜。也难怪那些漂亮的女人趾高气扬,即令她们的脑子里空空如也,其实都是让男人们惯坏了。明知如此,我还是不能免俗。作为象我一样高智商的男人,被哥们捧上了云台,没个花容月貌在旁无论如何是交代不过去的。我是个俗人,没有诸葛亮,秦少游的为知音舍红颜的雅量。
清的出现让我感到上帝对我真是青睐有加。
(二)
那天无聊,在校园的新华书店里找书籍消磨时间,一个长发披肩的倩影从眼前飘过,让我眼前一亮。那个女孩高挑清丽,眉宇间似乎一点淡淡的忧郁,反而给她添一些雍容的气质。
我正在琢磨怎样与这个女孩答讪,她却走到我的面前,问我是否要买我手中的那本书。哇,我感到一个吹气如兰的天仙降临凡尘到我身边一般,一时之间倒没注意她在问我什么。
“什么?”我怔怔地。
“噢,我问你要不要买你手上的那本书。”她一字一顿地说。
“书,什么书?”我低头看一眼,《美学原理论》,鬼使神差地,我不知道我怎么把这本书绰在手里的,而且还是架子上唯一的一本。真是运去金无色,时来铁生辉,那天一定是我的幸运日,一定是上帝安排好的我和清的邂逅之日。
我激动得有点眩晕,心里也暗骂自己骨头怎么这么轻,脑子里又在飞快地琢磨怎么让这美女对我一见钟情。
“这本书,姑娘需要吗?”我很关切地问。
“这是我下学期必备的参考书,你要吗?”
“当然,但我可以让给姑娘。”我故作姿态。
“那多不好意思。”她竟有些忸怩起来。
“没什么,我只是买了玩儿,再过俩月就飞美国了,弄点中文书填填行囊罢了。”我在特意地抓她的注意力。
这一招果然有效,我看到她的眼睛亮了一下。“留学还是探亲?在意我问吗?
”
“当然是留学,我还没有女朋友呢。”我感到自己有点轻薄无耻,但我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机会,该出手时就得出手。
她果然有了兴趣:“我也想办留学,不知道是不是很难。”
“不过是托福GRE,都是小菜。”我撇了撇嘴,刚过去的苦难已成行云流水。
“是这样,我是学文学的,联系学校很难的。”她一脸的无奈。
“哦?”我感觉机会在向我招手,“象你这么漂亮的姑娘,何必受那洋罪,想出国应该是很容易的。”
她没作声,脸却有些红了,那神态,那模样,简直就象一朵刚出水的莲花,让我心痒难耐。她就是清。
(三)
与清交往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能在联系学校和申请签证的煎熬中有个清在身边,真是我前生修来的福份。清是怎样的一个女孩,我说不清楚。对于我,她有着天上白云一样的高洁,山间泉水一样的清纯,枝头牡丹一样的雅致。在她面前我有时候觉得诚惶诚恐,她就象一朵冰花,我怕我的鲁莽的举动会不经意地伤害了她。
被她吸引一半是因为她眼中那一点淡淡的忧郁,可那点淡淡的忧郁却经久成了玫瑰上的一根尖刺,让我的心痛苦难当。
和清认识的时候她正在“失恋”的低谷,她交往了三年的男友在车祸中殒命,柔弱的清几乎崩溃。虽然事过境迁一年有余,她还是不能自拔,每次经过他们曾一起消磨过时光的地方,她都伤心得不能自持。女人也许真的和男人不一样,她们不能忘旧。清说她想离开这个让她伤心的地方,所以她也想到出国。
以后的我好象有了使命感,出国不但是为我自己,也为了清,为了带她离开这个让她痛苦的地方,这使命让我感到自己很崇高。
哥们都羡慕我的桃花运,对清的美貌赞不绝口。
和清走在一起让我有种怪异的感觉,从人们嫉妒的眼光里我感到满足,男人一生所求不过四个字:江山美人,江山可以引伸为才具与事业。对于我来说,事业也许还没有起步,但已经有了个好开端,才具我是从来不缺少自信的。如今再有美人在侧,我怎能不志得意满。
但也有更多人的“鲜花插在牛粪上”的不屑的眼光让我有自卑感,才华不象美貌可以穿在身上,也不象财富和权势,可以八抬大轿地抬出去。清太美太乍眼了,不在她身边不懂得被人看作是人间浊物的含义。
出国准备让我欠了不少债,但为了清,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临上飞机的那一刻,我忽然感到一阵空落。短短几个月的交往,匆匆忙忙的结婚,我不知道清对我到底有多少感情,我真的能拥有她到永远吗?
(四)
初到美国的我有一些孤独,但时间不长。我性格开朗,能吹能侃,再加上那点家学和幽默,朋友立刻纷至踏来。也有女孩子向我频送秋波,也曾让我心旌摇摇,但想到清,我还是稳住了阵脚。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只为了解决一时的寂寞,太不值得了。那些女孩子也有有姿色的,但跟清比起来,连狗尾巴花都配不上。
清的照片被人啧啧地赞叹着,说电影明星也只有那容貌,没有那仙子一样的气质。我自然得意一番,我对女人的眼光当然是没挑的。但隐隐约约的,我又有一种不安—我真的能拥有她一生吗?她那双含着清怨的眼睛总让我莫名其妙地感到心痛。
我不是个善于理财的人,我好面子,对朋友出手大方,也看不起那些在仓库商店里吃免费品尝食物还要几个人共用一个杯子占免费续加饮料便宜的同胞的行为。虽然我过了资格考试后拿了全奖,我还是入不敷出,欠了一大笔债。朋友们见我豪爽,也乐意借钱给我。我日夜盼着清来,也希望她能帮我摆脱困境。
一大把的电话费终于把清接来了,清出机仓口的时候,我都不敢认,这是我的老婆吗?她好象不是从飞机上下来,更象是从云端上走下来的。她好美,简直象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为这样一个女人再苦守几年也值得。和我同来接清的两个家伙,一个叫勇,一个叫峰,都欢呼起来:“哇,城兄真有艳福,清嫂子好个大美人那!”那个叫峰的已抢上一步去嘘寒问暖地献殷勤去了,让我不禁皱眉头。
清还是当初离别时的样子,不温不火,不冷不热,眼里仍然那一点清怨。是的,清怨,是我给她的那份哀愁的别名,那是清独有的忧郁,我从来没有在别的女人眼里见到过的忧郁。我很自信我的爱情会逐渐地驱逐那忧郁,清会在我的呵护下快乐起来。我不是个心胸狭窄的男人,我知道忘却需要时间,我更不会愚蠢到去嫉妒一个死人。
美人在怀是每个男人的梦,但我的心里却不踏实,总感觉象捧着个烫山芋。我一穷二白,又债台高筑,我惭愧不能给清一个美女应该享有的东西,我感觉对不起她和她的那份美丽。清说她不能要孩子,她要先上学。我同意,她还太年轻,她只有二十一岁,来日方长。但对于清来说,上学是要一笔学费的,这就意味着她必须出去打工。峰的老婆颖在餐馆里做企台(WAITRESS),说可以介绍清去打餐馆。我思来想去,餐馆工太苦了,实在舍不得让清去受那份罪。于是颖给清找了个看小孩的工作,清工作半年以后,终于还清了我以前的债务。清说,她需要开始给她自己积攒学费了,同时,她也开始准备托福和GRE。
(五)
我说不清我是否幸福。是的,清很美,美得让人窒息,她给我带来太多的虚荣,羡慕,以至于嫉妒,我应该满足。每次去朋友的聚会,不论是华人的还是美国人的,清都是中心人物,都有一群向她讨好献媚的家伙。
在华人中最突出的就是峰,峰很高大英俊,典型的北方人。峰和清大学是同校,常听到峰不无遗憾地对清说:“当初我们的宿舍楼紧挨着,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我真有上去给他一拳的冲动。峰的老婆是清的好朋友,都掩饰不住的醋劲:“是呀,当初你们认识就好了,我就不用在这里瞎掺和了。”为了我的自尊,有时候我不能不损清一句来提高一下自己:“就她那点智商。”都知道学文科的人不如学理科的聪明,我不能显得自己太配不上她了,我不知道也怕知道清听到此话时的感受。
女人在学语言方面总比男人有优势,她们的脑子好象就是为讲话造的。不到一年的时间,清的英语听说比我强出百倍。在美国人的聚会上,清也是注目的焦点,她的温文尔雅的气质,端庄大方的谈吐,无法不使我相形见绌。我的导师曾对我说,清在表达社交方面我是难望其项背的。我真恨上帝不公平,我的内秀远没有清的外秀更得人赏识。
和清的关系就象古语说的,相敬如宾。清总是与世无争,或更准确地说,自成一统,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我为此痛苦。唯一一次不快是我在家乡的弟弟要换大房子,向我要钱。我是个好面子的人,即使自己勒紧裤腰带,也要把帮朋友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更何况是兄弟。所以清曾说我适合做朋友,却不适合做丈夫,她也许是对的。明知道弟弟并不缺钱,只不过不想贷款付利息,我还是从清的学费基金里抽了一大笔钱寄去了。那次让清哭了好几天,因为那意味着她的学费又不够了。我也挺难过。
每次和清温存也些许让我失望,清从不主动,让我感觉她只是迎合我,在逆来顺受,感觉她并没有热情,这种感觉让我兴趣索然。我害怕问又真的想问她:“你到底爱不爱我?”
有一天午夜梦回,感到有人在啜泣,我扭亮台灯,竟然是清。她平躺着,泪水流进了她的耳轮,她竟然浑然不觉。我好生不快,她这是何苦?
“清,怎么了,我弄痛你了?”我有些不耐烦。
“城,不干你的事。我只是想起来他去了三年了。”清闭上眼睛,好象有些羞愧跟我提起这些。
“什么?”我的心在紧缩,天,她还是忘不了那个阴魂。作为男人和她的丈夫,我知道我不能表现出不满,那样会把她推得更远。我没有再言语,只是把清拉进我的怀里,紧紧地抱着她。
清在我的怀里叹口气:“对不起,城。”
“别说了,我理解。”我大度地说。
清在我的怀里象一只柔顺的羔羊。
(六)
清每天去图书馆看书复习托福GRE,然后再去打工。我们白天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
我在无聊的时候,便上网读中文。一个叫星潮的网站引起我的注意,那里有一些女诗人每天都在发一些爱情诗。情诗于我就象小孩子的游戏,我只在清来美之前在信中给她写过几首,都是古体诗。我看不上现代长短句,总觉得是无病呻吟和不懂音韵的人的附庸风雅。但那几个女诗人的哀婉的情诗却不知怎的打动了我,尤其那个叫青萍的,她的诗里透露出的爱而不得,又锲而不舍的泣诉好象也触动了我的软肋,总让我感觉她就是我的清。我爱上了青萍的诗,每天打开电脑的头一件事就是找青萍和她的诗。青萍的那些美丽而悲情的句子让我这个自诩七尺男儿永远刚强的汉子也有了心痛欲碎,欲哭无泪的感觉。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时。
我似乎明白了清实际上不爱我,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只是报答我,报答我在她失落的时候送她的一只肩膀让她痛哭,报答我带她离开那个让她伤心欲绝的地方,报答我对她的一往情深。那份曾让我着迷的“清怨”现在却变成了一根眼中钉,肉中刺,让我睡卧不宁。我感到我的忍耐已达到了极限,我再也装不出大度了。
那个晚上清的冷淡终于激怒了我,我一把把她推下了床,她的身体重重地落在地上,我有些担心,担心伤了她。我跳下床看她,她坐在地上哭。我无法克制自己心中的郁闷和欲火,我猛一使劲把床头柜上的台灯,闹钟和一台小电视一起扫到地上,耳边厢一阵东西碰撞和破碎的声音。我忍不住甩了句国骂,踢开门走了出去,我已经准备好了鱼死网破了。
我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听到清在收拾屋里的碎片。我忽然有种懊悔和悲痛的感觉,我回到卧室,帮清一起收拾干净。我对清说:“清,原谅我,我只是一时的冲动。”
“对不起,城,”她有气无力地回答,“我不太舒服。”
“清”,我扳住她的肩膀,“你到底对我是什么感情?”
“城,我好累,我们明天再说好吗?”
我绝望了,我知道清不爱我,我没法让她爱我,我在跟一个看不见的灵魂作战,就象跟风车作战的唐吉柯德,我胜不了。
(七)
不知道为什么,青萍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我对星潮便也失去了兴趣。认识秋让
我的生命再次出现玫瑰色,但我不知道那是福还是祸。
那天中午我陪老板亚力山大在学校附近的一家中餐馆吃饭。我们的服务生是个三十五岁左右的女子,跟清差不多高矮,很有风韵,身材玲珑有致,一张脸眉清目秀。她好象是个新手,英语不太好。也许是听不懂亚力山大带着希腊口音的英文,无论亚力山大问菜里有没有蒜,还是有没有葱,她都是答OK。亚力山大反而来了调侃的兴趣,问她:“OK是什么意思?”
“OK的意思就是OK。”她略带窘迫地答道。
亚力山大笑得前仰后合。我看不过去,向亚力山大陪个小心,对那女子用中文说:“我老板想知道菜里有没有蒜和葱,因为不希望下午和人谈话时有口臭味。”我向她挤了挤眼睛。
“对不起,”她脸红了,倒有几分少女的羞涩,“没有,都没有。”
亚力山大去上厕所的工夫,我便与她聊了起来,因为那家店生意并不好。她就是秋。
秋看上去很年轻,但已经三十九岁了,比我大九岁。她刚来美国不久,丈夫看上了个年轻的女人,就和她离了婚。现在她自己带着个十三岁的女儿。秋很大方活泼,好象生活的压力对她并没有多少影响。她说有了前夫给她的安置费和女儿的抚养费,基本生活还过得去,她只是打点零工补贴家用。因为英语不好,只能先在这生意清淡的小店里找工。
以后每隔几天我便去秋的餐馆吃顿饭,当然不是喜欢那里的饭菜,而是喜欢和秋聊天。和清比起来,秋更象个市井美女,她没有清那样大家闺秀,高不可攀的清雅,但她却有着清所没有的小家碧玉,平易近人的温馨。如果倒退十年,清与秋年纪相仿佛的话,我想我可能更倾向于娶秋而不是清。
秋的公寓就在附近,交往久了,她也请我去她家小坐。她的家很舒适干净,她是成都人,她做的川菜比那家她打工的餐馆要美味得多。秋说她有个弟弟和我同岁,我长的很象她的弟弟。她一口一个“城弟”地叫我,倒让我有种到家的感觉。
秋也有自己的烦恼,那就是她的女儿。她的女儿小玉才十三岁的年纪,已经天天吵着要交男朋友,因为她的同龄女孩子们都有男朋友,秋好怕她误入歧途而后悔终生。在这方面我没有有任何经验,我不知道怎么帮她。好在秋只是发发牢骚,好象并不指望我能给出任何建议。
秋的友谊带给我很多快乐,因为秋是个直率而快乐的人。
我总不自觉地拿秋和清比较。
清象一条一尘不染的清泉,水至清则无鱼,这话形容清正合适。在清的面前我有压抑感,她象一颗太亮太亮的明星,我在她的面前没有一丝的光芒。我的才华,我的潇洒,我的幽默感都在她的光芒里融蚀净尽,没有一点用武之地。
而秋则不然,她温和得象一杯温牛奶。我记得小时候我胃不舒服时母亲就用温牛奶抚慰我,温牛奶对我比任何灵丹妙药都灵验。在秋的眼光里,我看到欣赏甚至崇拜,同时,我又能享受到她的姐姐般的体贴入微。秋从不避讳她英语的不足,很感谢我对她的帮助。她快人快语,让我感到她身上与她年龄不一致的年轻人的活力。我在想,如果谁有幸娶到秋,作为男人应该满足了。
在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了秋。
(八)
华人的圈子总是是非多,我和秋的来往在学校已被传成了“姐弟恋”。有人骂我得陇望蜀,也有人骂我身在福中不知福。我自知和秋是清白的,也懒得理会。我不知道清是否也听到了什么风声没有,她最近正在考试的最后冲刺阶段。我想她知道了也好,如果她嫉妒,说明她爱我,否则我和她也走不到头了。
清选择的学校离我有五个小时的车程,理由是那所学校最好最便宜。而我明白,她想离开我了。送她走的那一天是在九月,她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秋好吗?”我知道我们的婚姻快走到头了。
在清走后的一次偶然机会,我发现了清的一些考试复习笔记。在笔记的背面,我读到一些诗句,那么熟悉,我想起来那是星潮网站上那个叫青萍的女诗人的诗。从清的几经涂改的字迹中,我刹那间意识到那个青萍就是清。我的心不自主的抽搐了一下,天,她在复习考托的同时,竟在图书馆里用电脑贴情诗。很明显,这些诗不是给我的,而是给那个天堂里的他的。我只拥有了清的美丽的躯壳,我从来没有得到过她的心。我感到愤怒继而屈辱,可我思前想后,清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反而是我对不起她,是我先背叛了她。虽然心痛,我想也许我该给她一个自由身了。
清走了,我和秋的接触也更频繁了。秋是个女人味十足的女人,在秋那里我感到轻松和愉悦,我得到作为一个男人的自尊和荣耀。唯一让我不安的是秋的女儿小玉,小玉很显然地讨厌我。每次我在秋那里留宿,小玉都会把门和桌椅拍得山响,然后再道对不起。我不知道怎样和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相处。
我找到一份薪金不菲的工作,打电话告诉清,清礼貌地恭喜我之后,说:“我想你也该和我离婚了。”
“什么?”我茫然,我不知道清已经在等这一天了。
“你很明白,”清的声音平静得可怕,“对不起,我没能给你幸福。”
“清,”我不自觉地眼睛湿润了,“我只想问一句,你是不是从来就没有爱过我?你给我的只是感激。”
“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我只是想知道,死也要死个明白。”我的声音开始哽咽了。
好长一段沉默,我听到了清的哭声:“对不起,我,我忘不了他。”
一切都明白了,一切都得到了证实,我恼羞成怒:“为什么,为什么?我没有他漂亮,没有他温柔,没有他有才华,没有他对你好?”
“别,别问我,”清泣不成声,“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你怎么这么傻?”我只有摇头。
(九)
我不知道和秋会怎样,我只有三十一岁,而秋已经四十了。她依旧很美,美得根本不象四十岁的女人,但我不能确定我是否应该娶她。流言我倒不怕,但我想要自己的孩子,而且不止一个。秋却说打死她也不能生了,生小玉就差点要了她的命,而且那时她还年轻。于情于理我都不能不给她个名份,我知道我爱她,她真正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女人是水做的骨肉。我也知道她爱我,她用她自己的钱为我买东买西,除了对她女儿外,她对自己都是很吝啬的。于是我决定向她求婚。
“城弟,”出乎我的意料,她竟然说,“我觉得你应该娶个和你年龄不相上下的女孩,我已经四十了,女人过了四十就老得太快了。我不想让人以为我是你妈。”
“秋,你?”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城弟,”她顿了一下,“你还太年轻,你会后悔的。小玉也无法接受你做她的后爹。”
“原来如此。”我颓然地坐在沙发上。
秋和小玉搬到外州去了,说是为了小玉上个好点的学校。我知道,这里面另有原因。她走的时候,正是秋叶黄落的时候,和清走的季节一样。我的心也象落叶一样飘零。
我好累,我突然间想不通为什么男人都爱美女,除了那份虚荣还有什么?爱情和美貌真有那么大的关系吗?现在的我只想有一个爱我,尊重我,踏踏实实地和我一心一意过日子,生儿育女的普普通通的女人。
一年以后,我回乡娶了一个别人介绍的相貌平常的女人。不久,我有了一儿一女,老婆对我一心一意,我在工作上也小有成就。我的生活很稳定。
听说那个叫峰的家伙离了婚,一直追清。清却至今没有再婚,不知道她是否还念念不忘她的初恋。秋后来嫁了个也离过婚,有两个孩子的医生。我所能做的就只有祝愿她们幸福如我了。
 | |
|